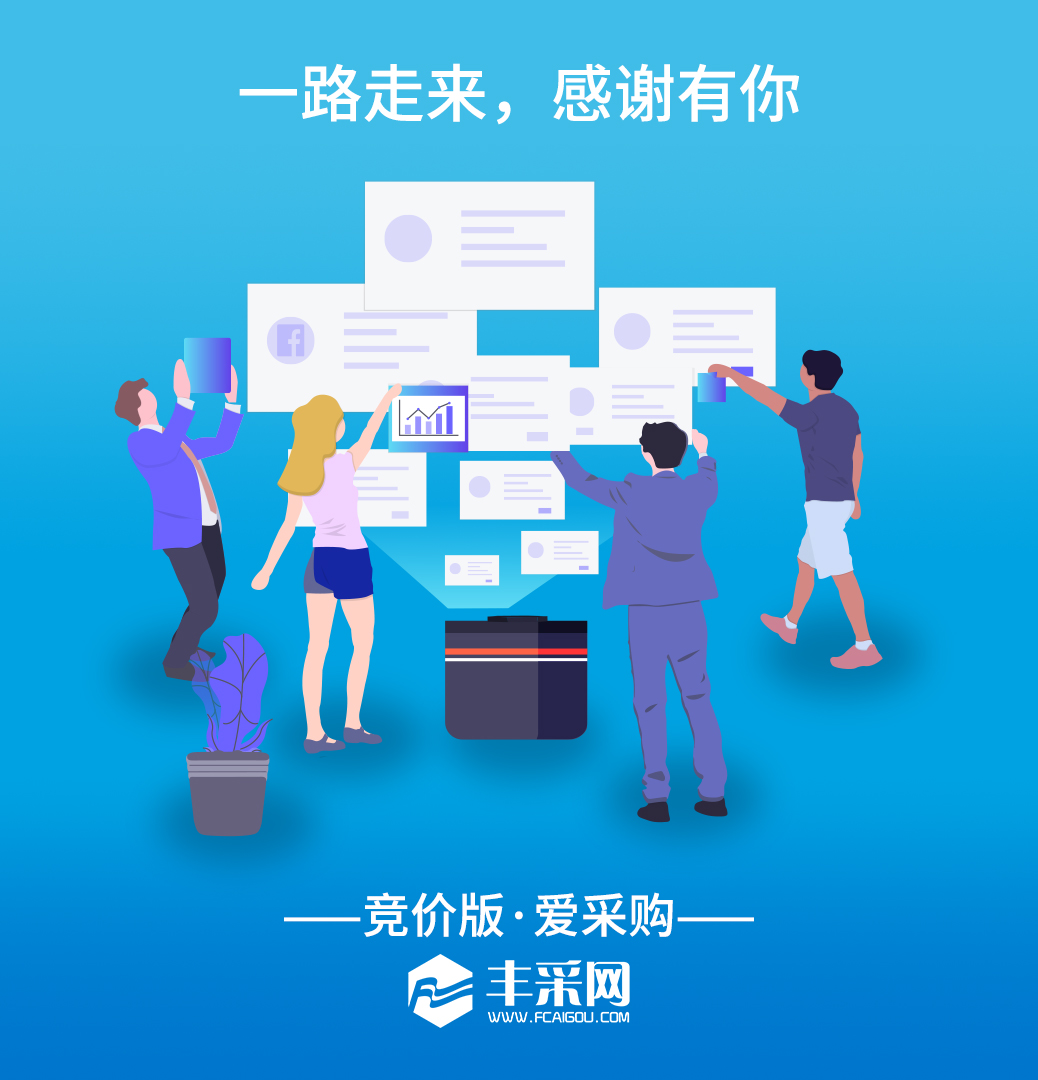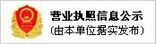俄烏沖突事件讓我們看到了科技力量的重要性。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要擁有自主的核心技術,并且要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尤其是新的形勢下,更要通過創新驅動,繼續塑造發展優勢,不斷提升競爭力水平。
“但科技自立自強不等于封閉起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對新京智庫說,而是要在全球開放的背景下去實現。畢竟,現在知識和經濟一樣存在分工,一個國家不可能什么都自己研制出來,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造出來。
在具有天然國際競爭態勢的數字經濟時代,要保持我國的數字經濟競爭力,我們又該如何增強科技自主?新京報采訪了相關專家來試圖解答增強我國科技自主需要解決的幾個主要問題。
持續加強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問題,這在很多專家學者看來都是一個首先需要補齊的“短板”。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告訴新京智庫,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很快,顯示出一定的先發優勢,不過應該意識到,這種優勢不一定能長期保持下去。有數據表明,我國數字經濟的增速已經放緩。現在看來,我們國家容易被人“卡脖子”主要是在數字技術基礎方面,比如芯片、基礎軟件等。
這與我國長期以來的基礎研究投入不足有關。2021年10月,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在第87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上公開表示,我國基礎研究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研究投入不足。
新京智庫梳理發現,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從2003年的87.7億元增加至2020年的1467億元,年均增速高達87.37%。雖然從投入規模來看增長很快,但投入強度仍然比較低。以2020年為例,基礎研究經費仍只有當年GDP的0.14%。而全球主要創新國家的該項投入水平是在0.4%-0.7%。
作為創新國家的代表,美國還在進一步提升其相關投入。2022年2月,一份2400頁的《確保美國科學技術全球領先法案(2021年)》(The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與其他相關提案合并成《美國競爭法案》獲得美國眾議院審議通過。后者包括一系列條款,其中520億美元用于芯片制造,450億美元用于改善關鍵產品的供應鏈,1600億美元用于科研和創新。
這被認為將確保美國在制造業、創新和經濟實力方面處于領先地位,并能夠在競爭中勝過任何國家。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員劉小平對新京智庫表示,美國在基礎研究改革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同時美國現階段采取的科技封鎖政策也對我國基礎研究的發展設置了巨大的阻礙。因此,我們需加快落實發展基礎研究的政策。
實證研究也能證明加強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葉菁菁團隊通過爬蟲抓取從1997年至2016年所有自然科學基金立項項目相關信息,最后樣本涵蓋1997—2009年168個城市7類學科的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金額和與之對應的高校專利、校企專利以及企業專利的申請數和被引用數,樣本量為3312份。
葉菁菁告訴新京智庫,具體來說,如果一個城市的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總量每增加10%,該城市對應技術領域的申請專利總數隨之增加1.2%,相對應技術領域的專利被引用數量增加1.49%。
作為知識創新的重要載體,專利數量和引用量的增加說明基礎研究投入不僅有利于促進更多的實質創新,同時也提升了創新的質量。由此可見,“基礎研究是重大技術創新的基礎,其最大效益是通過突破性的科學發現,并經過長期演進,形成高質量的專利技術,支撐創新驅動發展”,葉菁菁說。
具體而言,數學學科是一門在數字經濟時代需要加強研究投入的學科。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宗本則認為,數學作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石,不僅為人工智能提供新的模型、算法和正確性依據,也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可能性提供支持平臺。數學與AI領域的合作需要進一步加強,通過模型彌補數據的不足,通過數據優化模型。基于數據的人工智能和基于模型的數學方法,只有這二者結合,才能得到很好的結果。
劉小平認為,基于物理學在發展量子信息科學技術中的重要地位,我國應繼續發揮物理學在該領域的支撐作用,繼續發展天文學與天體物理、粒子物理和光學等優勢學科的已有學術影響力,同時加強凝聚態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和光學物理與量子信息科學技術的學科交叉研究,加強發展這兩個學科中的重要研究問題。
發揮企業的示范作用
在諸多專家看來,下一步需要充分發揮企業在科技研發,尤其是基礎研發中的示范作用。
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中心王煉撰文表示,企業已成為我國科研活動的絕對主體,但企業對基礎研究重視不夠、投入不足的問題依然非常突出,導致企業難以有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也無法更多地掌握關鍵技術和技術創新活動。企業基礎研究薄弱,致使企業難以獲得相應的知識儲備和能力積累,難以提高吸收能力,也不利于產學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轉化。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剛告訴新京智庫,應充分發揮企業在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鼓勵具有較強技術創新能力的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設立專項資金,加快推動具有應用場景的基礎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
劉剛還介紹,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是美國創新體系一個重要特色。這種主體地位有兩重含義:企業不僅是科學研究的主體,而且是創新決策和投資的主體。從美國企事業R&D(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看,聯邦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投入資金基本保持在較低的水平,平均占總企事業R&D的10%;而企業的研發投入金額占總企事業R&D的80%,接近聯邦政府的8倍之多。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王軍亦表示,企業是市場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供給主體,是促進科技創新的攻堅力量。應調動各類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真正使其在創新中發揮主體帶動作用,提升創新的質量和效率。
王軍建議,要運用市場化機制鼓勵企業創新,引領企業加強對基礎研究的研發力度。比如,鼓勵領軍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健全科技成果產權激勵機制,完善金融機構投資監管體制。重視中小企業在創新中的地位,將R&D經費更多投向中小微企業。“通過稅收優惠、資金補助等措施激勵各類企業和資本投入基礎研究領域,形成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民間企業等多元共同創新的模式,激活創新活力”。
王煉亦認為,政府部門需完善現有政策體系,酌情通過稅收信貸等手段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積極引導和支持企業開展基礎研究活動,同時鼓勵企業與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更為緊密的合作關系,聯合開展基礎研究工作,產出高質量的科學技術成果。
破除人才流動“中梗阻”
專家也表示,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還有數字經濟發展時代下的相關人才問題。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經濟相關核心產業既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崗位,但也意味著人才缺口。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陳煜波認為:“如何吸引和培養新階段所需要的人才,是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中建立競爭優勢的重要基礎。”
2016年12月,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發布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測,2025年,僅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就將創造就業崗位2000萬人,但人才缺口也將高達950萬人。
面對這種形勢,僅僅靠目前國內的教育還是難以培養出與之相匹配的人才規模。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程撰文表示,我們還需要準確把握全球人才競爭的新態勢,大力探索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雙重沖擊下全球引才新路徑。比如強化源頭引進,著重引進國際頂尖大學資源;破除人才流動“中梗阻”;率先創設“求職簽證”,就地引進優秀的外國理工科博士、博士后;對標國際與市場規則。
對于數字經濟相關人才的爭搶,國內很多城市已經在出臺措施。2022年2月23日,中國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在立法會上做出的書面答復稱,為便利人才來港,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快速處理涉及輸入非本地人才來港從事研發工作的申請,當中涵蓋13個科技范疇,例如金融科技、5G通訊等。杰出創科學人計劃則加大力度資助大學吸引國際知名的創科學者和其團隊來港參與教研工作。香港特區政府亦會進一步增加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年度配額,并探討擴展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至涵蓋本港大學在大灣區所設分校。
劉尚希亦建議,我們還需要建設一個好的體制機制,以激發數字經濟人才的創造性,并且能更好地把研發成果市場化,從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尤其是要加大改革開放力度,“要有改革的緊迫感,尤其是在科技體制方面改革的緊迫感。”